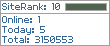入到菜園新村,一見到鞦韆架賴恩慈就一臉興奮地喊:「我好叻好叻玩鞦韆㗎!」
非常人語
獨腳戲 賴恩慈
2012年10月11日 ~~ 第1179期 香港《壹周刊》
九月的最後一天,記者會正式公布新一屆十大傑出青年的得獎名單。一身黑衣的賴恩慈走了進來,同樣黑色裝束的工作人員開頭不以為意,還以為這個嬌小的女生是後台同事,因為其他的獲獎者穿得那麼耀眼,或純白或彩色。這抹黑彷彿有點不尋常。
掌聲響起,獲獎人陸續上台致辭。輪到她了,賴恩慈撫平衣服上的皺褶,緩緩走上台,像一名演員步往屬於自己的舞台,唸出和別人不一樣的台詞:「我希望政府真正可以為人民服務,可以阻止地產霸權,可以推出真普選,可以停止推出 23條,可以撤回新界東北、中港融合,可以撤回國民教育。」她雙手交叉舉起:「我希望將來可以提名黃之鋒做傑青。」
這就是賴恩慈,獨立電影《 1+1》的導演編劇,「好戲量」劇團的主席。說起來她廿九年的人生也有點像戲:不足一歲,親生父母離婚,將她送回鄉下託人寄養;六歲返港由一對老夫婦監護;在監護人的藤條責打中偷偷演話劇;在一片質疑聲內,拿着政府資助拍菜園村的故事《 1+1》。人生如戲,幾乎每一幕她都踽踽獨行;每一幕她都有個特別的名字。
這天賴恩慈帶我們回菜園新村,她拍《 1+1》講述的是建高鐵、拆菜園村這個大環境下兩爺孫的小故事,因為取景和村民們混得很熟。原來的菜園村終究是拆了,遷到更偏僻的新址。
在村子裡接待我們的游伯年紀不小了,走起山路卻仍矯健,邊走邊大聲說話:「嗰齣戲呀,我有睇㗎,爺爺同埋個孫女呢!好開心呀,我哋成條村都出去電影院睇咯,哈哈哈,好叻!」
傍在他身邊的賴恩慈也笑:「我拍這部電影就是希望有一天整村人可以一起看,當成一份禮物送給菜園村。」
Mogat Lai
拍完《 1+1》之後,賴恩慈( Mo)成立了「一毛製作有限公司」,因為電影中一毫子是個重要象徵。
「戲內的爺爺存一毫子,他不是存錢,而是存他的記憶。存下每一日他對一毫子說的話,或者這一毫代表那天發生的一件事。香港現在很多看似沒有價值的事物,其實只是大家沒保存珍惜,像菜園村,那時為了經濟上的價值捨棄這條村落,好像一文不值。所以,我用『一毛』這名字提醒自己。」
讀浸大傳理學院電影電視系出身的 Mo,畢業後做舞台劇,也當過大半年的香港攝影節項目經理,不是不想拍戲,只是實在沒有資金。
《 1+1》得以開拍是因為她參加了藝術發展局舉辦的「鮮浪潮短片競賽」,每個參賽小組有四萬元預算。
「藝發局是政府機構,我套片擺明反政府,拍的時候 team member都說:『哇!你拍這題材都沒想拿獎啦!』嗯……確實是,但我還是想拍!」
結果《 1+1》拿下「鮮浪潮大獎」和「鮮浪潮二○一○國際短片展最佳電影」兩項大獎,之後陸續參加近二十個國際影展,去年五月,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近五個月。
「完全沒想到有此成績,拍攝中唯一一下我很想拿獎,是聽說如果拿到鮮浪潮大獎,影片會即場播放,而拆菜園村的相關官員當日會出席!」社會議題永遠是她創作的最大動力,結果獎拿到了,當日官員卻沒有出現。
提名 Mo參選傑青的,是《 1+1》中的「爺爺」楊秀卓。她和這名藝術老師在六四、七一遊行集會中相識,「他本身對菜園村好關心,選角時我不想找一個演員『扮演』關心這件事,我想找個對這件事有情感的人。」因為拍戲,楊秀卓逐漸了解 Mo在舞台劇、紀錄片等方面的付出,便提名她參選。
電影與人生的軌道交錯,相互糾結影響,像當初的一兩句無心之言,誰也不知道會一語成讖。
「『一毛製作』除了因為電影裡的一毫子,也因為我的英文名字叫『 Mo』。說起來很『淤皮』,中三那年讀英國文學,教課的外籍老師一進門就說他記不住中文名,要學生即場為自己起英文名。我馬上想: huh?為什麼我要為了方便你而改名呢?結果輪到我了,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,根本沒去想英文名。我站起身,跟他說我英文名是『冇嘅』,全班大笑,那老師就以為『冇嘅』是個名字。」從此她多了個英文名「 Mogat」,後來又簡化成「 Mo」。
「 Mo」音譯似「冇」,又似「毛」,是一無所有又一毛不值的,卻又最自由,也最豐盛。
中學時期賴恩慈還有個花名叫「賴堅持」。
「同學話我真的好鬼死鍾意堅持,我下定決心的事,別人多麼反對我都會做。」
如果不是這麼倔強,她的人生恐怕安穩許多,也乏味許多。
參加話劇是個意外。中學讀的是名校庇理羅士,功課測驗奇多,一年級老師還點名叫她寫劇本參加話劇比賽,「我想她覺得我平時口多,要罰我。」
結果一接觸就愛上了,「那是很大很大的一次啟發。透過做話劇,我拯救了我自己。
「我細個是不開心的,從小就有很多問題,總是被罰,但我把這些問題放到創作裡,大家又覺得幾得意,找到一點位置,所以我很相信這世界沒有垃圾,只是被放錯了地方。」
上月三十日的十大傑青獲選名單公布,賴恩慈穿一襲黑裙到場,闡明自己反國民教育的立場。(《蘋果日報》圖片)
○八年,有網民不滿好戲量阻街,發起「將好戲量踢出旺角」行動,之後好戲量檢討並改變了街頭表演的模式。圖為 Mo有份表演的《吉蒂與死人頭》在旺角街頭上演。(《蘋果日報》圖片)
她醉心話劇,監護人卻激烈反對。「中學玩戲劇是被人打住來玩的,排戲回來就會被打一次。」她想了想又補充:「也不是每次都用藤條打,有時罰企……我都預咗,只是看罰『 Mo』。說起來很『淤皮』,中三那年讀英國文學,教課的外籍老師一進門就說他記不住中文名,要學生即場為自己起英文名。我馬上想: huh?為什麼我要為了方便你而改名呢?結果輪到我了,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,根本沒去想英文名。我站起身,跟他說我英文名是『冇嘅』,全班大笑,那老師就以為『冇嘅』是個名字。」從此她多了個英文名「 Mogat」,後來又簡化成「 Mo」。
「 Mo」音譯似「冇」,又似「毛」,是一無所有又一毛不值的,卻又最自由,也最豐盛。
賴堅持

透過戲劇為社會發聲一直是賴恩慈的創作動力。
中學時期賴恩慈還有個花名叫「賴堅持」。
「同學話我真的好鬼死鍾意堅持,我下定決心的事,別人多麼反對我都會做。」
如果不是這麼倔強,她的人生恐怕安穩許多,也乏味許多。
參加話劇是個意外。中學讀的是名校庇理羅士,功課測驗奇多,一年級老師還點名叫她寫劇本參加話劇比賽,「我想她覺得我平時口多,要罰我。」
結果一接觸就愛上了,「那是很大很大的一次啟發。透過做話劇,我拯救了我自己。
「我細個是不開心的,從小就有很多問題,總是被罰,但我把這些問題放到創作裡,大家又覺得幾得意,找到一點位置,所以我很相信這世界沒有垃圾,只是被放錯了地方。」
她醉心話劇,監護人卻激烈反對。「中學玩戲劇是被人打住來玩的,排戲回來就會被打一次。」她想了想又補充:「也不是每次都用藤條打,有時罰企……我都預咗,只是看罰什麼。」
直到這對老夫婦去世,他們一次都沒看過她的表演。
即使如此,還是堅持。大學時她參與當時新成立的「好戲量」劇團,成為核心成員,○三年開始在旺角街頭表演。「好戲量給我很大啟發,○三年發生很多事,沙士、七一遊行,原來社會的變遷從街頭出發,而做藝術就是參與社會,不是躲在排演室排戲!」
所以他們走上街頭,與路人互動,和警察周旋,用戲劇為社會發聲。「賴堅持」陸續參與不同劇作:討論香港教育制度的《陰質教育》、諷刺警權的《意外死亡》,乃至近期分析女性定位的獨腳戲《神奇女俠》、《女兒紅》等。
監護人去世後她無家可歸,蝸居九龍殯儀館旁邊唐樓的「好戲量」排演室。沒有家,她唯一能捍 衞的,是瑣碎的身外物,包括利是封、火柴盒、玻璃瓶、中學時期同學送的毛公仔……什麼都捨不得扔,一個個紅白藍堆在角落。直到兩年前拿獎學金往英國列斯大學修讀戲劇表演碩士之前,她在這個人來人往的排演室足足住了五六年。
賴恩慈
「賴」是她的本姓,「恩慈」卻是後來監護人幫她取的名字。「我的女監護人是退休教師也是基督徒,她總說是靠着神的恩典領養我。」她認真地雙手合十閉目仰天:「我為此感謝祂!」
六歲那年她被帶回香港,父母將她的監護權交給一對老夫婦,她從此有了新的名字新的家,然而在她口中,他們永遠是冷冰冰的名詞「監護人」,那個家也是「他們家」。
「實在太清楚自己是寄人籬下,太知道他們不是爸爸媽媽,他們領養我時已經六十多,是阿爺阿嫲的年紀了。但我的男監護人影響我很多,讓我從小關心社會議題。
「他以前應該是行船的,懂五種語言,也很關心國際新聞,我在他家沒得看任何娛樂節目,純粹是六點鐘新聞、 BBC News。我當時的概念是電視只有六點、六點半、七點的新聞節目。」他留給賴恩慈最親近的記憶是,他指着地球儀,告訴她新聞上說的國家城市是在哪個地方。
《 1+1》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,菜園村村民特意出市區捧場。
《 1+1》的兩名主角,「爺爺」是藝術老師
楊秀卓,飾演孫女的簡慧賢卻是賴恩慈
在旺角做街頭表演時認識的小觀眾。
賴恩慈是創意藝術中心( JCCAC)的駐場藝術家,她的工作室牆上用黑漆繪滿花草人像,「開頭 JCCAC說你只能髹牆不能畫花喎,我說你就當我髹了兩種顏色不就行了?」
這是一個清心寡慾、有諸多教條的家庭,賴恩慈骨子裡叛逆,嘴上從來不敢頂撞。大學二年級從英文轉系到電影電視系,早就先斬,卻遲遲怯於後奏。
「大學選科時監護人要我聽話選英文系,他們覺得至少能做老師有份安穩職業。當時他們已經老了,開始擔心離開之後我真的沒了依靠。
「結果我還是從英文系跑了出來……轉系後不久,男監護人得了癌症,他躺在病床上問我:『你將來打算怎樣?』我一直逃避這個問題,直到他跟我說:『如果我打直出番去,我會行去睇你表演。』我才告訴他:「我轉系去讀電影了。」他那句話是這麼多年來唯一一次 approval,令我條路走得沒那麼歉疚。」
可惜男監護人再沒能從醫院走出來,一年後,女監護人也撒手而去,賴恩慈只感到難過,卻沒有無措。「這是從小到大的一種訓練,訓練我獨立,所以他們要疏離。我覺得他們真的好愛我,他們領養我時已經知道這是十幾年的事,不是一世人,所以早就計劃好了,讓我可以承受那種傷痛。」
監護人有自己的兒女,他們逝世,賴恩慈就搬走,只帶走了一個黑膠唱碟機,和男監護人的地球儀。
賴香香

小時候通山跑的賴恩慈來到菜園新村就像放生,很快和游伯討論起田裡的白菜香草粟米。
六歲之前,她一直住在廣東茂名附近的鄉下,騎水牛、撿牛糞、滿山地跑,也沒上過幼稚園。照顧她的是村子裡一位婆婆,婆婆喚她:「香香。」
「哈哈哈,不知是覺得我香,還是我整天在屎堆裡想我香一點。我和婆婆的關係很好很好,她不識字,卻教會我很多人生道理。
「我細細個會想,我的爸爸媽媽不要我,我沒用才不要我的,所以自己是垃圾,婆婆告訴我:『你諗吓,連你的尿我都要你存,然後淋番落泥土,跟住我哋又食番啲菜呀。』只有她才會這樣真實地告訴你道理。那些理念一直承載着我,令我有任何挫折都會沒事。」
來香港後,她每年都回去探望婆婆,直到中學三年級,婆婆去世。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經歷死亡,也是我首次經歷歇斯底里的悲傷。」
少了這個伴隨自己長大的人做後盾,六歲前的美好時光從此真正過去,成為一段回憶。
「我一直覺得六歲前那段時間很重要,我接觸的所有東西都來自大自然,讓我整個人平和,而且樂觀,所以面對逆境時我很容易開心起來,六歲之前在我心裡是個樂土。我知道世界上有個美好的地方,雖然這只是記憶,但美好的回憶是藥,能幫你治癒一些傷痛,我慢慢搣,到現在都未搣完。」
六歲前婆婆對賴香香說的小道理、六歲後監護人指給賴恩慈看的地球儀、中學賴堅持排戲後迎來的藤條炆豬肉、還有阿 Mo送給菜園村的《 1+1》,這些回憶都是「爺爺」手中的一毫子,存起來,便有了重量,和價值。
有了這些,人生的舞台即使獨行,便也不至孤單。 
撰文:周榕榕
攝影:鄭樹清、高仲明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