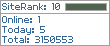這一刻,幾乎全暴露了。一個中年畫家的過往。 15年裏書寫下的長信私話,今天一一展示。本來與友人的傾談,是處在迷茫歲月裏的慰藉,如今看來,竟是人生的索驥。失憶與記憶的片斷,在紙墨之間閃回,時光再怎麼荏苒,那時的苦痛,酸楚,狂妄與歡樂,還歷歷在目。撰文:鞠白玉攝影:李彥剛
放大圖片 
張曉剛, 1958年生於中國昆明, 78-82年就讀於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以《草原組畫》開始在中國當代藝術界嶄露頭角, 94年創作《大家庭》系列作品,並以此參加當年的第 22屆巴西聖保羅雙年展,獲得國際關注,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代表人物。代表作《失憶與記憶》系列,《裏與外》系列等。目前為中國藝術界最具盛名的藝術家。 10年出版《失憶與記憶——張曉剛書信集》,展示人生軌迹。
大毛請原諒,我就像個夢囈者,嘮嘮叨叨個沒完。沉悶孤寂的生活,黑暗的歲月,使孤獨者最後的權利似乎只剩下自白了。說這些不僅僅意味着某種悲觀,虛無的情緒。現實就像我們每日必進的午餐,沒有誰能夠拒絕,本來如此,長期如此,並非今夜所致。剛兒 1990年 11月 7日
放大圖片 
■ 81年與周春芽去四川草原寫生近兩月,共畫了三百多幅作品。
放大圖片 
■ 84年,於藝術家毛旭輝(右)畫室。
書信人生索驥
所幸他和他的友人能保存下當年的信件,他和他們一樣珍惜着從前。出版的這本書信集,就像一場人生的坦白。我是帶着這本書信集去敲他工作室的大門。上次見面是五年前,他在舊工作室的最後一天。那時他忙碌焦慮,形容自己身陷一個系統裏。正當紅,人人想去見他,他這人其實言語木訥,常常詞不達意的。不久前他在三亞度假,時常在網上發微博,我在上面看他行蹤,原來只是每晚看一部好電影。難得的消閒時光,他比從前懂得珍惜時間的運用。他們到底是拿甚麼來換取今天?曾經也只不過是個失意者,處處透着不合時宜,對現實總是充滿疑問,被當時的主流厭棄着的這般人。當時他最大的願望,是有一點點錢,一點點假期,從昆明歌舞團的工作裏解脫出來那麼一刻,去草原上,去大山裏,吹着冷風寫生,和他的友人們,能夠深夜裏烤着火,喝着酒,暢談着人生。那時的孤獨夜夜啃噬着這些靈魂,個個像被空置於世,大學時代那藝術家般的狂想,放進真實的生活裏,引來的是嘲笑聲吧。他年輕時是個性格清冷的人,格格不入的書呆子氣,那幾位摯友天各一方,惟有寫信,聊慰情愁。「覺得離過去特別遠吧?」我問他。「非但不覺得遙遠,反而相當地近,近得就像在昨天呢。」他說。「這些全拿出來需要勇氣嗎?」又問他。他笑了,「這只是小部份,還有一些信關於私人的情感事,因為關係到別的當事人,就不能分享了。」
和未來的人會面 放大圖片 
■血緣:大家庭 3號( 95年)
巨幅的未完成的作品,將兩千平米的工作間填滿了,兩面大型的照片資料板,是他多年的工作習慣。上面有他收集或偶得的心儀照片,也有家人的留念,女兒學校班車的時刻地點表也釘在上面。以前他就說過,心裏常有一個畫面,是女兒幼小時,他帶她在昆明的河邊走,黃昏的太陽光灑在水面上,父女間的溫情,是他那段灰暗生活裏唯一的亮。甚麼樣的照片圖像能打動他?我看多數是處在灰黃色彩下的孤獨的人,他們直視於人,像是拍下的那一刻,知道有一天會和未來的人會面。就像他的作品,那些收藏家們都想得到的畫面,中國人的面影,一個大家庭或一個個體,目光清澈,面容上有淡淡的胎記,像訴說着回憶。他比從前健談了,不是因為志得意滿。從容也許是因為過去與未來之間突然開了一扇窗,清風習習。出這本書信集,也回頭望這 15年的點滴記憶,他和他的幾位珍貴老友,從青澀時就那樣熱烈地通過紙筆討論着人生與藝術的意義,給生活賦予了那麼多形而上的東西,直到今天也沒全然放棄。而且全靠那時的堅持和勇氣,得到這刻的所謂成功,財富名利,沒有甚麼愧然的。數月前,印尼收藏家以五千多萬元購得張曉剛名畫,欣喜之下辦了一個慶祝晚宴。 16年前,張曉剛給某個代理人寫信,懇求對方先預付三萬美元。他那時想在成都安一個像樣的家,也需要一個幾十平米的工作室,三十萬元對他來說可謂天價。他在信裏寫:如果能行的話, 11月你來便將錢帶到重慶,我一定以一張《全家福》來感謝你。也只不過十數年,境遇自是天壤之別了,他由渴求安穩生活而作畫的窮藝術家成為今天炙手可熱的明星。然而他承認中年危機,那危機是方向感,成功而後的迷失。他需要找尋一些東西提醒自己從何而來,才知向何而去。
沒書信是遺憾
我問他如果有時空穿梭,最想回到哪一段日子。他選的竟是八十年代在昆明歌舞團任職美工師時期。那時分明他又憤悶又貧窮啊,只是一心想能去田野裏風餐露宿地畫畫。可他又能在那段記憶裏咂摸出一段美好來,若不是那時的孤寂滋養他,不是有那些時間去聽他鍾愛的 Pink Floyd,去讀尼采,卡夫卡和薩特,去日日夜夜剖析自己的心,可能也難識清自己是誰。 18年前初赴德國看卡塞爾文獻展,那是百般受阻之下得到的機會。給當時的美術評論家栗憲庭寫信,洋洋灑灑幾大篇,難掩興奮。別的中國藝術家看了展覽,心裏是頹唐掉了,覺得做現代藝術怎麼去和西方人拼,他卻看見了曙光似的,終於知道路在何方。大開眼界之後,「心裏竟然生出了使命感」,他現在還記得那種情氛。現在的人都羞於談使命,他當時卻是毫不諱言。那使命感撐着他走後來的路,直到今天。個中曲折不必多提,反正到現在西方藝術界都知道中國這個張曉剛。這些年來他在國外屢屢大展,同行介紹他的時候總是用華麗的語言,他形容是:就像是在介紹另外一個人,和我自己沒關係。「你坐在別人的沙發上,聽別人在談論你的故事……」有時他恍惚地從現實中出離,覺得不踏實,將這一段話寫在一片鏡面上成為作品。他在國外連開兩個講座,強調一個真實的張曉剛,他覺得摘去光環後一派輕鬆。人生兜兜轉轉,既漫長又短暫,他珍惜眼前,他和老友們也常聚,談論的話題和當年卻也無異,仍然是藝術,哲學,理想,他們到達不到彼岸的終極,所以探討的東西常常是迴圈。他慶幸仍有這幫摯友還願意延續着當年的習慣,只是從 96年開始,大家已經不依賴紙筆,沒有書信的日子,到底是便利還是遺憾?
放大圖片 
■巨幅的未完成的作品,將兩千平米的工作間填滿了。
放大圖片 
■失憶與記憶( 03年)
放大圖片 
■失憶與記憶( 07年)
放大圖片 
■天堂 2號( 10年)
放大圖片 
■史記 3號(水泥×銀色簽字筆。 09年)
放大圖片 
■工作室內一直都有這樣的資料板,上面有他搜集的照片,也有女兒學校班車的時刻表。
放大圖片 
鞠白玉,滿族女,八十後,達達主義者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