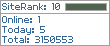非常人:看不見的《十三釵》 聆聽第五代耳朵
在 1978年,當陳凱歌選擇當導演,張藝謀選擇做攝影師,陶經卻選擇了北京電影學院錄音系。由 1987年《孩子王》開始,他便成為兩位老同學的「第五代耳朵」。二十多年來,兩導演在兩極聲音中徘徊,而陶經所採集過、創造過的 soundscape,其實可能比個人化影像,有更複雜層次、更多遊走空間,也就更可聽。於是我也選擇用耳朵,聆聽陶經的《金陵十三釵》。撰文、攝影(人物): Lo其他圖片由陶經提供
十三釵的霧與槍 放大圖片 
■教堂玻璃窗是個重要的象徵。
採訪在北京西城區的「和聲創景」——全中國唯一有認證杜比環迴 7.1的混錄室,也是《金陵十三釵》後期聲音製作室。陶經和他的同事,挑了三場戲,讓記者用耳朵體驗電影。首先是電影開場:還未化身為神父的小混混基斯頓.比爾出場、女學生在圍城中逃難。我閉上眼睛,專心聆聽,聽覺比視覺可有更多想像,但在如此混亂狀態中,聲音焦點是甚麼?「在戰爭中,有很多聲音可以表現,比如呼吸聲、腳步聲、飛過的子彈聲、遠處槍炮聲,但最後提煉出來的,只有兩或三個聲音。最符合這故事 atmosphere和背景的是,霧裏的槍聲。」陶經說,「霧,讓人喘不過氣來,有種永遠跑不出去的感覺;因為霧這種意境,有點不太現實,使子彈很慢地飛過來成為可能性。通過霧的介質,遠處傳來的槍炮聲,有點不太正常,濕濕的、悶悶的。」霧的聲音怎麼做?「霧本來沒聲音,有點像毛毛雨打在樹葉上。但我用比毛毛雨再小一點的水珠互碰的聲音,這個霧,大概混了七八種聲音。」另外兩場,是子彈穿過教堂玻璃窗的兩槍聲。「第一槍,非常殘暴的子彈,打死一個十幾歲的生命。所以打碎玻璃的聲音,特別清脆真實;第二槍,拯救了被強姦的書娟,背後加上兩種風鈴聲,如果是純粹子彈撞擊玻璃,就沒這層意思了。」記得在之前的宣傳中,陶經說過,第二槍象徵人的記憶——那一刻會永存書娟記憶中,所以加入寫意的風鈴。「我本來想在日本人吹哨前就停了風鈴聲,後來再延過來,就是要加強一點印象。人的感知是很奇怪,會閃回。那一刻,書娟的臉,好像喘過氣來, safe了。」這個「陶瓷風鈴的回憶」可不簡單,他的三位年輕助手,花四個月時間,從現場錄音、素材庫和玻璃部門的幾百個聲音實驗中,刪掉太髒太實不好聽的,最後挑出十多個聲軌混成。如果不是陶經解說,耳朵沒受過專業訓練的觀眾,根本分不出是霧是花,而且人的五官,眼睛最發達,甚至過份發達。「我們的感知, 80%是用眼睛, 20%才是耳朵。但看電影不是要看說明書,觀眾只要感覺到點點不一樣,就 OK了。」至於聲音和影像的關係,他說,不能是老公老婆,吵完架就離婚。「它一定是個整體,等於自己跟自己,有時是相反,就像自己有兩個想法, to be or not to be,我要做這件事,但理智告訴我不要做;有時畫面跟聲音,完全一致。」
放大圖片 
■電影開場時跑不出去的霧。
放大圖片 
蝙蝠俠的聲音
從背景回說到主角。在視覺造型方面,觀眾看見張叔平王家衞式的旗袍,但主角的聲音可有甚麼特別設計?「因為這電影比較寫實,所以沒過多的設計或象徵性東西。我們盡量保持演員的個性,他自己塑造的角色,他要表演的聲音,所以要盡量靠近 location的聲音,因為對人物來說,這是最準確,最有表現力。像基斯頓.比爾那個等級的演員,一定認為自己的語言是其表演的很大一部份,因為這是我的 show。」一個人怎樣說話,他的聲音某程度上反映他的內心,即使演戲,也騙不了人。特別是對陶經來說,聽過的聲音比任何中國人多,沒甚麼能逃過他的耳朵。「人的聲音,不在於好聽不好聽。電影裏,你只要很真誠的說出來就好,最怕你假,像某些香港演員,一聽就知在演戲。但有的人說話就是很真實。」那麼聲音也可以是電影的靈魂嗎?「不可能,除非是部特別的影片,比如拍一個盲人,他看不到外面的世界,或者他理想中的世界是怎樣,那就可以說是 soul。」蝙蝠俠的聲音有多真,大抵電影的畫外音都驗證了,至少他不是中國人期待以為的荷李活大明星,他只是個演員,非一般的演員。陶經曾提到比爾經常手執 walkman,「他可以買一車最新款的錄音機,但為甚麼還要一個 walkman?我認為,他是個 artistic style的演員,所以他這個人,非常敏感。他媽媽好像也是戲劇演員,可能從莎士比亞傳統一直演下來,教他有關表演的元素、表演的偉大,所以他很認真,有些傳統習慣,很難改變。他是屬於內心的演員,需要內心去激發他一些東西。可能開始拍電影時,別人教他用 walkman,他跟導演說戲,說完後拿回去聽,糾正錯處,那麼一個 walkman不讓自己分心,他不 care別人會不會笑他,所以我最欣賞他對物質的態度。」
哥哥與發哥 放大圖片 
■「張國榮去世前的冬天,來北京見我們《霸王別姬》老班底,希望能幫他一起做他導演的新電影。左一是張進戰(後來《赤壁》的執行導演)。」
聲音可以很抽象,但語言卻實在,它反映的是文化背景,一個思維體系。作為中國大片第一次以國際級演員當第一主角,而且要以英語展示它的全球化野心,團隊當然特別重視西方觀眾對英語的感覺,所以專門找了李安電影的 dialogue coach,糾正中國演員的英語發音,有時糾正表演的情緒。「因為,即使發音準了,但感覺不對。感覺不對,戲就沒了。」說到像我這樣「普通話 system不很好的人」,要假裝北方人,那就要一句句重新學習怎樣說話。我只能回應,這反映真實的狀態。用普通話演戲,對香港演員來說,也是最困難部份。「香港演員來中國拍戲,非常害怕說話。」所以劇組會提前把標準普通話正音,給他們練習,給他們糾正發音。比如張國榮在《霸王別姬》(部份由別人配音)、梁朝偉、張曼玉在《英雄》,還有發哥。不過,陶經說,經過糾正後,發哥在《黃金甲》裏的普通話,說得特別好,沒人會反對。「那時候拍《霸王別姬》批鬥一場,張國榮、鞏俐、張豐毅,三個角色在批鬥,幾個人指着鼻子罵。張國榮罵鞏俐時說,『八七年』、『八七年』。當時我都驚了,甚麼『八七年』?其實他要罵鞏俐是『潘金蓮』。所以就容易引起笑話,就像《臥虎藏龍》,要是拿原版在大陸放,大陸觀眾就不會感動,會經常發笑,最感動的時候,大家可能就笑了。」這是語言的問題,但文化差異還是較難解決。
放大圖片 
■陶經和發哥在《黃金甲》拍攝現場。
放大圖片 
■陶經和 Leslie在《霸王別姬》現場。
電影的時局
從 1987年《孩子王》到康城最高技術獎的《搖呀搖,搖到外婆橋》、從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音效《英雄》到《功夫之王》、從奧運開幕式到《十三釵》,雖然經歷了從文藝到商業大片兩個很不同的年代,但陶經每次的參與,其實都有他自己的聲音實驗,希望帶來新鮮感。比如《英雄》中萬箭齊發一場,加入了海豚和鯨魚叫聲,讓聲音更有生物性;《霸王別姬》程蝶衣台上一場戲,畫外音包括拆舊戲園和人群批鬥的聲音,更重要是永遠無人接聽的電話鈴聲;《搖呀搖,搖到外婆橋》,他專程借來美國四十年代的話筒來錄鞏俐唱歌,沙沙的味道,有種古老年代的溫暖;《孩子王》中,陶經堅持採用同步錄音,收集了大時代農村中各種環境「雜音」,也可說是曾上山下鄉的知青——陶經的個人記憶。如果說,電影是不同年代的反照,那麼他如何看四分一世紀中國電影的變化?「電影,一定跟時局有關係,它反映人的生存狀態、大家關注甚麼,以至世界的局面。我認為,比較大的變化,還是技術的革命,它讓電影的拍法和詮釋方式,有了改進;電影的 language和 grammar,有了更廣泛的可能性。雖然現在有 3D,但電影的原則,從 1978年我上電影學院到現在沒有變,學生仍然在學習克拉考爾( Siegfried Kracauer)的理論,大家仍在這個沒有變化的電影原則中做電影。」雖說技術提供更多可能性,但現在去戲院看大片,好像只剩一個形容詞:「震撼」?「震撼這個詞,確實是近幾年才需要,我們看電影原本不需要很大聲,這就是人的觀念和時局在變化,你不震撼人不去了。另外網絡可以 download很多稀奇古怪東西,包括遊戲也很震撼,那電影還不震撼,你就沒飯吃了,對不對?所以,電影是跟人發展到這階段的感覺有關。」對,所以《金陵十三釵》絕對是中國 2011年時局的折射,而電影的畫外音比故事情節更吸引,如圍城中的大霧,聽見遠處悶悶的槍聲,卻永遠走不出去。
放大圖片 
■陶經和鞏俐在《活着》拍攝現場。
放大圖片 
■陶經和陳凱歌在《荊柯刺秦王》拍攝現場。
放大圖片 
■陶經和張藝謀正在拍攝一部城市宣傳片。
放大圖片 
■ 2003年香港電影節《英雄》獲最佳音效。

■陶經在很多採訪中,不時提及自己是上海人,所以很實際。但在 1978年選擇錄音系的文青,怎說也不會是很實際的人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