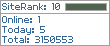政府近日推出兩幅私家醫院用地招標,香港大學醫學院亦想分一杯羹,十劃未知有幾多撇,但可以肯定這是院長李心平明年退休前最後的大項目。
四年前,醫學院風雨飄搖,李心平臨危受命做院長,以局外人身份擺平各個「山頭」。這一仗,他「醫」好了醫學院,但他覺得「醫」好學生更重要,「醫生是healer,但很多時我們也是wounded,我們的傷口由誰來處理呢?」
每天面對生離死別,不少醫生會看化,卻不等於沒牽動情緒,文學和音樂彷彿成為李心平的「特效藥」,撫平內心的傷口,「喊過無數次,有時眼淚在心裏流,只有寫書法、欣賞詩詞歌賦、彈結他,才可令我心境平靜和減壓。」他把這套「獨門醫心術」傳授給學生,原來他傍身的必備良藥,不是止痛丸,也不是抗生素,竟是一支毛筆、一本書和一首詩。
「眾多詩人中最喜歡李白,簡直是神來之筆,伴我度過不少痛苦日子。」過去幾年,他在港大醫學院迎浪而上;驀然回首,李白在《行路難》中寫道「長風破浪會有時,直掛雲帆濟滄海」,大抵是李心平的寫照。

李心平每當沉醉在書法中,總能把一切煩憂和壓力忘卻。他手字絕對見得人,謙虛的他卻說:「只是塗鴉,難登大雅之堂。」
一臉慈祥的李心平,說話和行路的速度,比在醫院見慣打衝鋒的醫生要慢得多,寫書法時更將他文質彬彬的一面表露無遺。他捲起衣袖,不徐不疾的磨墨,提起毛筆寫的是北宋詩人黃庭堅的《書寒山子龐居士詩》,「這首詩描寫得黃河好美麗。」他一落筆,記者也不禁屏息靜氣,剎那間他的世界彷彿只有這首詩的文字,不容別人打擾。
寫書法對他來說,不只興趣咁簡單,「出外公幹時,袋裏定有一卷紙、幾支毛筆和墨,當別人在酒店看電視,我就在房寫字,寫完就丟,不需要有任何牽掛,好開心簡單。」寫書法令他心境平靜,他嫌楷書太過古板,喜歡寫行書,還曾跟國學大師饒宗頤拜師學藝。「本來想學寫草書,但他看完就說:『心平教授,你太注重結構,不能做到好瀟灑』,我以為自己好狂,原來都是太束縛。」李心平笑着說。
饒宗頤看穿了他,李心平的確規行矩步,喜怒不形於色,巨大壓力都靠寫書法來克服。「尤其是大戰前夕,有時寫半小時,有時寫幾小時,都不願睡覺。」他口中的「大戰」,包括重要的演講、課堂和辯論;記者覺得他其中一場「世紀大戰」,還包括○八年重返母校做院長,擺平亂局。

四年前,港大校長徐立之(右)請李心平返回母校,接替梁憲孫(左)任醫學院院長,擺平院內的「山頭」。物是人非,李、徐二人將於明年約滿離任,梁前年已轉投養和。

所有醫科生實習時都經過「執仔」的訓練,李心平仍清楚記得當年見到一個新生命誕生的興奮莫名。
神奇工
當時醫學院正值危急存亡之秋,既有「山頭主義」作祟,復又爆出前院長林兆鑫侵吞公款的醜聞,令醫學院聲譽大損。李心平的任務是撥亂反正,令醫學院得以重新上路。事過境遷,他不願在自己臉上貼金,無論記者怎追問,他只輕描淡寫的說:「當時醫學院是艱難時刻,我返來有特別任務。無論一個機構或組織,在演變中必定有整頓、調節和重建,這是十分合理的事。」但實際上有幾亂、他做過甚麼或有何感受,他統統封口不答。
空降港大醫學院前,他在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做講座教授,本身是著名肝膽科醫生的他,兼任教學醫院腸胃科部門主管,行醫超過三十年。最初由美國返港教書,他對很多事都看不順眼,「好多人向我投訴,話入到房醫生只望住電腦,無耐性聽他們說話,但我們做醫生應該做個好的聆聽者,要理解和同情病人。

中五會考那年,李心平的爸爸因肺癌過身,令他下決心當醫生,改變一生。

在學生面前,李心平好像爺爺般親切。對於明年離任,他安慰捨不得他的學生說:「若生命是一本小說,每個章回都有開始和終結。」
「病徵永遠只是表面,你話頭痛,但我不知道你爸爸是酒鬼,他和媽媽經常打交,哥哥被人捉去坐監,如果我不明白這些背景,開止痛藥給你是無用的。醫生是個神奇的職業,我們有特權令病人將所有喜怒哀樂和期望交給你,而你又可以幫到他們,我不希望學生或同事視之為工作,只為了報酬。」
一講起做醫生的使命感,李心平即變得滔滔不絕,他着重的不僅是醫術,更在乎醫者要有父母心,希望學生從病人身上聽出痛苦,所以他打破百年傳統,將人文學科的元素加入課程中,去年與文學院合作,成立全亞洲首個人文醫學中心,培養學生的文學和藝術情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